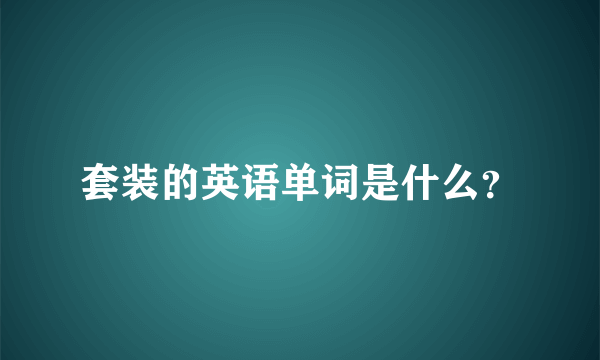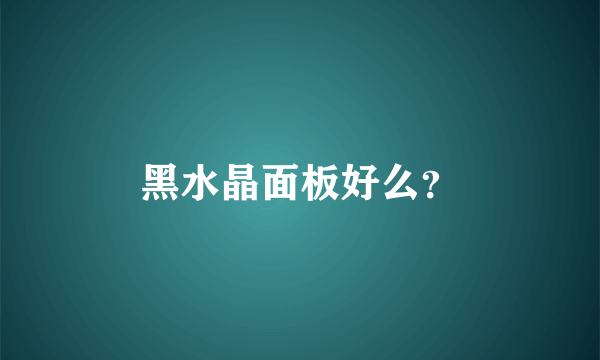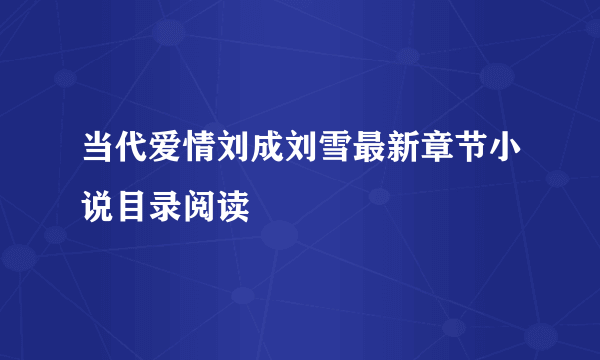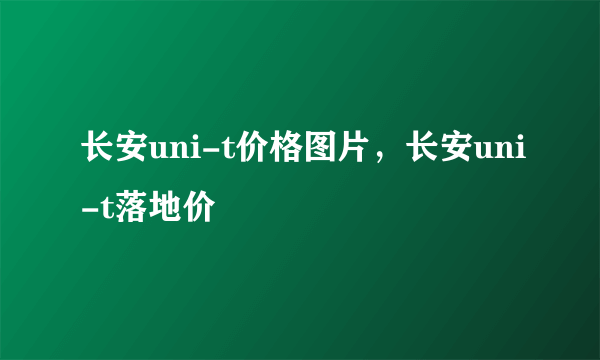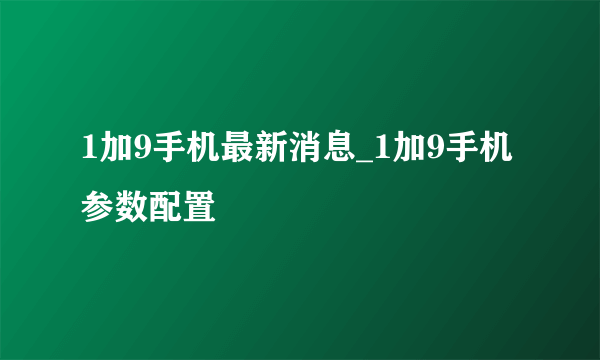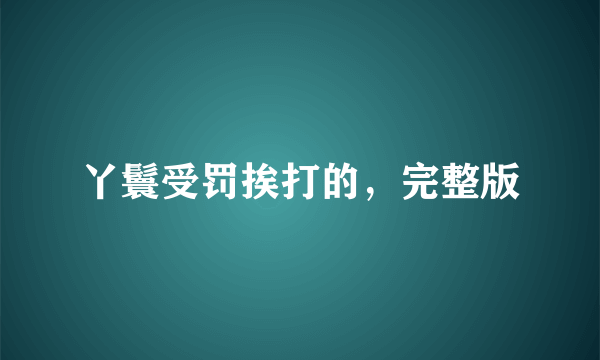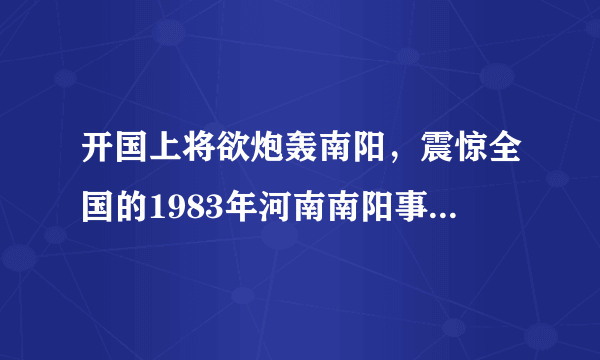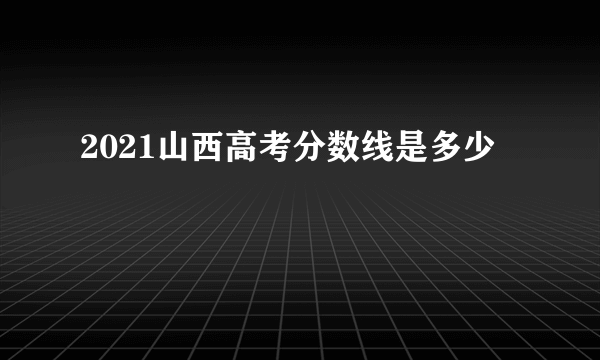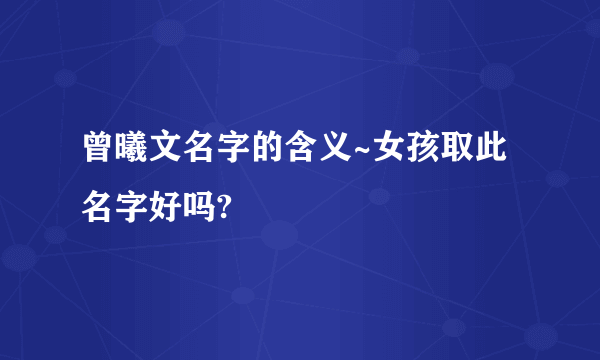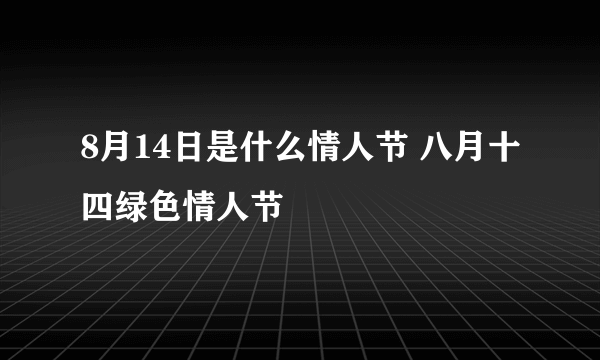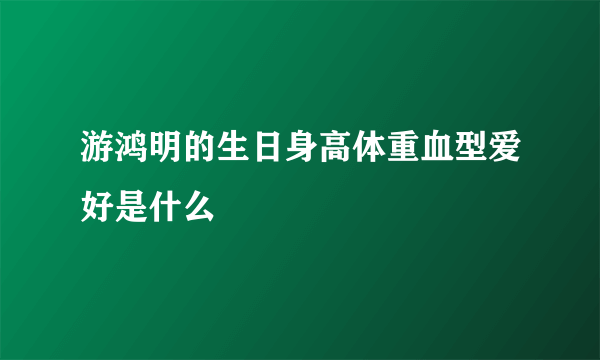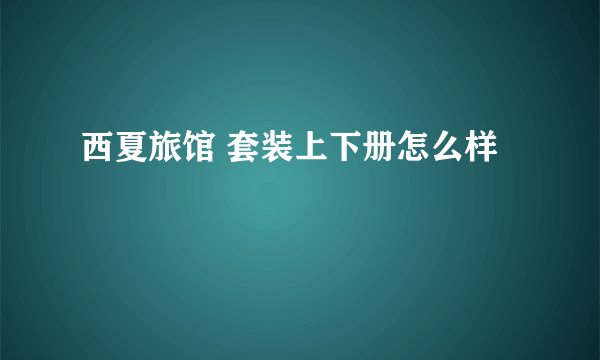
经验和历史的修辞幻术 ——论《西夏旅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 骆以军在《经验匮乏者笔记》中说过,“五年级(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一辈人)作者是人造人,是悬空走故事棋盘而无倒影之人,是经验匮乏之人。”而《西夏旅馆》便是骆敬献给经验的灵堂之上的一场盛大悼亡。这许多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满是以历史为名制造的忧伤的虚构之机器,看似复杂繁琐的修辞到头来竟是诉说尽处的空寂和虚妄。而在这部小说中,民族志(西夏的历史)和家族史(图尼克的家族历史)具有某种对应的结构关系,这其中涉及到的不仅是异族的覆灭或流亡,还有纵向的夫对子的遗弃和子对父的背叛,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充斥在每一个有时间存在的地方,甚至父子和夫妻。然而,这种敌意在破碎的时空、多种话语的声音和修辞幻术之中变成了失焦的经验游戏,在想象的叙述中,历史、时间和伦理关系都有了“物”的层面的意义。破碎的时空在文本、历史和现实之中悠游,而最终使得时空从漂浮的文字中消失了。 昨天 空间 现在 当骆以军说起西夏,甚至说起蒙古,以及回鹘、吐蕃、宋人、契丹的时候,他无疑在说台湾,准确的说,是在说台湾的外省人。同样是被驱逐,被命运流放,不得不踏上流亡的路途,从此一切过去都只能想象,这些无数个人的经验被历史抛弃,从此他们只能在另一个地方看原来的故土渐渐成为前世的原乡。而对于那些第二代的外省人,自从父辈死去,原本是他乡的台湾从此便成为了故乡。 西夏旅馆不仅仅是一个旅馆,它是作者用记忆和词语建造而成的一座时间繁殖机器,甚至是盛放历史和过去的神龛。在这座旅馆中,所有人都是流亡者,他们从别处来到这里,寻找记忆和时间,甚至是令人欢喜又悲伤的欲望。所有人都是真正的词语的流亡者,从作为引语的古老的西夏历史文献,到生硬的报纸文字,从李元昊到宋慧乔,甚至是和历史古书中的人物同名的图尼克和安金藏,记忆在词语上留下了最繁杂的痕迹,这些不同时空的词语代表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当它们杂糅在这里面的时候,令人感觉到:时间消失了,只剩下真空中的时间碎片。 西夏旅馆就好像美兰嬷嬷一样,“她是这个世界(在旅馆外活跳跳仍在发生、进行的)和那些墓穴棺椁般的故事之间交叉隐喻的神秘中介。”旅馆是联结昨天和现在的特殊空间,人们(这些在“迷离满溢神谕的重回原乡之旅”上漫游的异乡人)入住其间,便是在进行一种精神的救赎。无论是西夏,还是旅馆,或是原乡,都只是“一个曾经建筑在时间针尖上的幻术帝国”,他们像历史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不得不去流亡,不只是在现实中,当多年过去他们(他们的儿子们)发现时间对于他们变得不再平常,更像是一种幻术,无论是时间(增殖机器),还是词语(修辞术),都是一种幻术,一种用以使自己进入迷幻状态以重拾过去的绝佳方式。他们真的就好像从一出生便有了永远无法救赎的原罪,体内是漫流而无定的时间之河。那种命运般的大风化作了语言的狂欢,如同庄子所说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然而语言的背后却是无法言说的悲伤。 原乡 他乡 故乡 朱天心曾说,父亲朱西宁去世之后,台湾就彻底成为了她的故乡。原本受业于张大春的骆以军后来暂时抛弃了原来的对后设小说的执念(但实际上张大春在语言上的影响从未消失),从朱氏姐妹那里学来了一种语言背后的沉郁,虽然表面仍是语言的破碎的狂欢。无论是朱氏姐妹,还是张大春,或者骆以军,台湾对于他们,总隔着一个无法撇开的人物——父亲,这最初的外省人,带着对祖国大陆的回忆与对家乡的思念,让这些外省第二代作家有了一种遥远的家国想象。永远是隔着父亲遥望(父亲的)故乡,他们在新的道路上,看这些“行道树”。龙应台在《大江大河1949》中说道,“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漠的失忆来对付你。”在 失去了自己的家国之后,父亲用剩下的一生来寻找那个词。 有趣的一点是骆以军的小说里也提到了“老灵魂”,如同朱天心在《古都》中所提,而空间也从张大春的公寓沿着古都到达了旅馆。美兰嬷嬷作为知晓旅馆历史的人,成为了时间的代名词。然而实际上旅馆又是没有历史的,美兰嬷嬷也成为了摆脱了时间的形象。在旅馆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和空间,都在演绎不同的故事,旅馆便不仅是时间的繁殖机器,更是故事的繁殖机器。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其中之一便是没完没了的西夏。无数的人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到了这里,这让人想起了一九四九年的台湾,特别是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名词——眷村。无数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至于无数的故事联结在一个点,又似乎完全无所联系。 对于外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来说,他们是没有故乡的,他们只有父亲和祖先,他们只能在他乡遥望父亲的故乡,也许和父亲一起,但却独一无二地将那父亲的故乡认作了回不去的——原乡,无论何时他们都处于精神的流亡之中,在肉体的流亡之后,他们开始体会到时间和空间慢慢失落的痛苦,他们只能不断进行一场盛大的想象和悼亡。 西夏 旅馆 台湾 无疑,旅馆将两个完全陌生的时空世界联结起来——西夏和台湾。甚至每当骆以军说起西夏,他都是在说台湾,他想要凭空造一座时间和空间的旅馆,使无数人入住其间,以自我想象和对历史的想象进行一场冻结时光的精神救赎。作为最后一个“西夏人”,图尼克游走于混沌之中,甚至是姓名,甚至是他的父亲,以及他的过去。当他在一个不知何时何地的现代旅馆中说:我是最后一个西夏人,他实际上在说,“我”便是最后一个知道故乡和历史秘密的人,父亲的故乡将在“我”这里彻底终结,“我”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甚至是种族,西夏人早已经在历史的发展中灭绝。 在这里,骆以军想要通过书写野蛮以对抗文明的虚无,对抗历史,对抗当下。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来为台湾的那些忧伤的人招魂,包括他的父亲和家族。旅馆就是“虚无与流浪者后裔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便是一座被幻术和自我想象欺骗的仿逆之城,在这种城中,一个已经摆脱了时间和历史的人——图尼克,想要再次摆脱种族和一切可以摆脱的东西。胡人图尼克,手持一本词典与造词幻术,背后是遗忘所带来的恐惧,也许历史何其相似,那个因历史的误差而被集体灭绝的国度——西夏,不正是由那群刚坐稳江山便被别人打败并且追逐的流亡者在最后的孤岛上组成的最后的“祖国”吗?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他的父亲便是一切经验的终结者,便是历史的尽头,而他,只是从历史中逃离出来的幸存者,只能看着父亲和无数的流亡者一样,被时间和历史判刑,甚至在判刑之前便开始了一场缓慢的屠杀。 台湾是没有历史的,正如书中所说,“我必须要说,在这幢旅馆里长大的人,是没有‘历史’这个概念的。我们通常是在个人生命经历了蛮长一段时光之后,回头审视、归纳,才会轻微惊讶,喔,事情是在哪些时候发生了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里旅馆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繁华盛景,每一间房都住了人,来自大江南北各个行业的人们,在这间旅馆中交换各自的故事。然而如今旅馆中只有故事的残骸,人们从故事中跑出来,也从历史中跑出来,但他们终究是要失败的,他们只能看着自己陷入时间之中无法自拔,好像被诅咒了一样。他们远离了故乡,便是告别了祖先,他们的行为将给他们的后代自出生之日起便无法摆脱的原罪,即使他们书写,或是试图改变历史,也无济于事。 故事 历史 现在 依旧是在虚构和现实、过去和当下之间徘徊,骆以军带我们穿越故事和历史,甚至是伪历史,回到当下,然而有时我悲伤地发现:当下开始趋向虚构,而过去愈加真实。骆以军的小说便是一场危险的幻术,不仅仅是修辞与造字,也不仅仅是时间繁殖,更是试图将历史嫁接到当下,将故事和现实联结,以至于现实最后也成为了虚构的一部分,而我们依旧生活在变异了的没有时间的伪历史中。 现代的人是经验匮乏的人,骆以军说过,我们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我们是人造人。在小说中,历史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人物是从历史中剥离出来的,他们在当下与历史之间来回穿梭,而当下的确也是一种虚构。 “是的,像此刻。” “图尼克对女孩说:我正在盖一座旅馆。很怪的是,我用了大量的隐喻。” 骆以军用经验与历史的修辞幻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建造了这座神龛一样的旅馆,然而旅馆并不存在,或者可以说,旅馆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形状,它甚至隐藏在每一个台湾人的内心深处,那是对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去向何处的无所归属的深深的恐惧,饱含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忧郁与狂想。无疑他在进行一场交易,或者说:兑换。他想要用“现在”兑换历史,想要用“当下”兑换“过去”,想要用“故事”兑换“真实”,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了,只是到最后才发现无论是无奈的徒劳还是幸福的快慰,都只是冷暖自知。
标签:上下册,套装,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