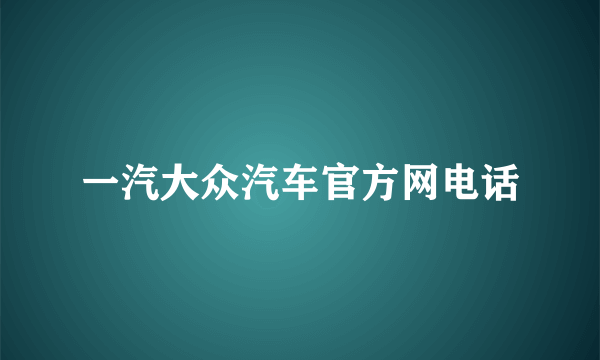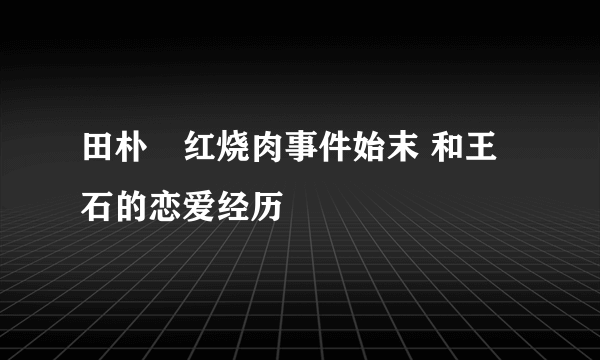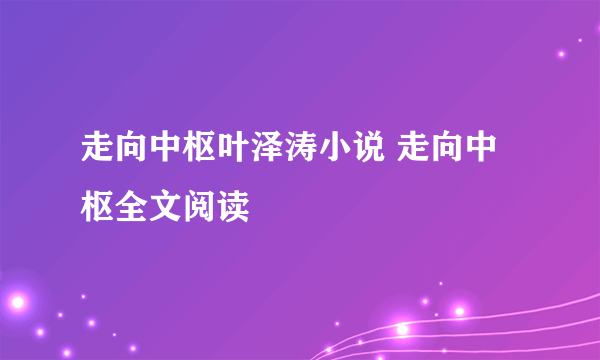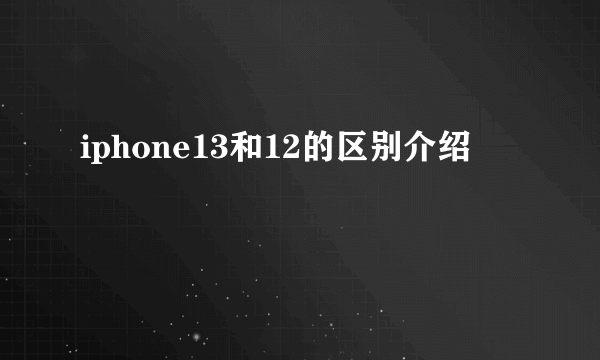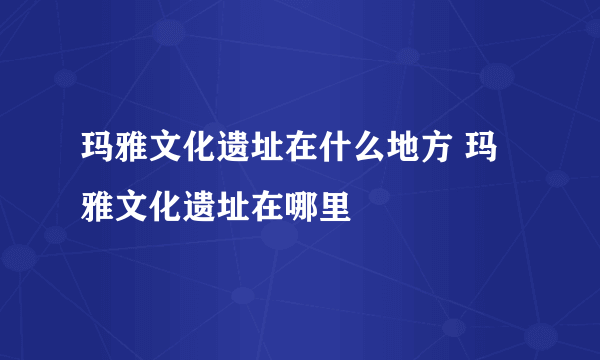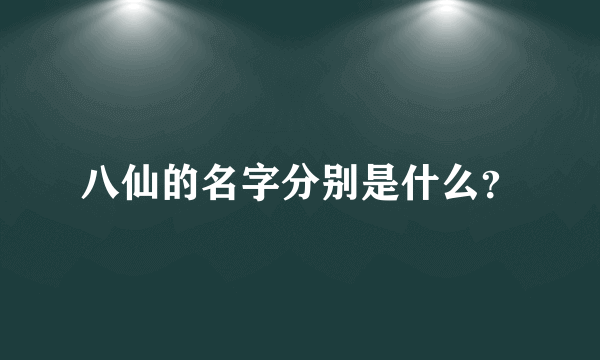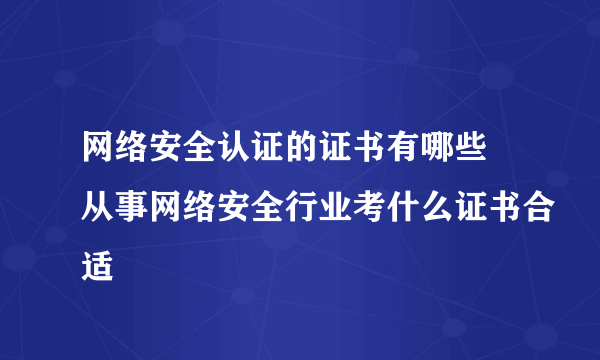山东斗法文本 (刘宝瑞先生述)
明朝永乐年间,北京前门大街五牌楼石柱子上头,贴着一张皇榜。前三门外人烟稠密,商贾云集,皇榜往外一贴,惊动了大街上过路的士农工商、五行八作。一百两十行嘛,也有做官的、为宦的、背弓的、挂箭的、推车的、挑担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丽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这些人不知道国家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贴皇榜,都争先恐后围着看。
就在这个时候由北边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孙叫孙德龙,他是东四牌楼猪市大街卖肉的,也会捆猪宰猪,山东登州府的人,四十多岁儿,好喝酒。这天刚打南市上回来,胳肢窝夹着个搭猪的钩杆子——这是白腊杆子,有核挑粗细,五尺多长,头里有两个铜钩子,猪要是跑了,离着它五尺,一搭就搭回来——这手提溜个钱口袋,这边胳肢窝还夹着账本,腰里系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把锡蜡的酒壶,擦得是锃光瓦亮,穿着个布棉袍,可已经变成缎子的了。怎么回事哪?因为他切完肉也往上抹,切完油也往上抹,日子一长,就跟现在理发馆那钢(gàng)刀布一模样了。
这天他下了市,刚打酒铺喝完酒出来,喝得酩酊大醉,走道脚底下直拌蒜,嘴里说话也不利落了(山东口音,下同):“这个酒哇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睁眼看不见道儿,简直是活见鬼儿!”走到皇榜前头一看,围着一圈子人。“咱借借光!”他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瞧是榜,他不认识字,他要问问,拨拉那位。“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说:“你慢着点,欠点岔了气!这是皇榜。”“什么叫皇榜啊?”“皇上家贴的!”“你念念我听听好吗?”“可以,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琉球国前来进贡,明为进贡,实为派老道了义真人前来斗法……'”“行了!行了!你别往下念了,你念了半天我一句都不懂啊!”“我白念了。”“我先问问你头一句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怎么叫‘皇帝诏曰’?”“皇帝说话就叫‘皇帝诏曰’。”“噢,皇上说话就叫‘皇帝诏曰',那我要是说话呢?”“……那,不知道什么曰了。”“好!你往下念吧。”这位想:我别念了,念完了再讲受不了,干脆我告诉他这意思得了。“琉球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派了个老道来,他会打三十六手哑谜,会念七十多本《金刚经》,找咱们中国人斗法。如果赢了他,他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赢不了,或者没人跟他斗法,那就得他们琉球为上邦,我们大明为属国。现在皇上贴皇榜选能人,如果有人会打哑谜会念经,跟老道斗法赢了的话,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大官封多大宫。你问这个也没用啊,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
这句话行了,孙德龙外号叫“万事通”,不论什么事,你要是说他不行,当时就急:“你别说了!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打哑谜,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念《金刚经》?”“噢!您会啊?”“我不会我能长个脑袋吗?”“哎呀!您会那更好了,您赶快撕皇榜找老道斗法去。”孙德龙刚要过去撕,那位想:先别忙,我得给他念清楚喽:“皇榜上写着老道会打三十六手哑谜,您会那么些个吗?”“他会多少?”“三十六手。”“咱会七十二手。”“嚯!比他会的加一番!老道会念七十多本《金刚经》。”“我那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那您就撕皇榜吧。”“我够不着。”“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搭猪的钩杆子。”“您不会拿它钩吗?”“对!”嘶!他把榜给钩了。看榜兵丁一瞅醉汉撕皇榜,抹肩头拢双臂给绑上啦,推着他去见榜宫。
榜官是解学士解缙解大人,孙德龙到这儿立而不跪,冲解大人一撇嘴,一抬下巴额:“我说你姓什么?”解大人一听:要过我一堂怎么着?“我姓解。”“解大人,你讲理不讲理?”“怎么回事?”“找老道斗法去,难道说就捆着去吗?”“哎哟!您是法官哪。”赶紧就埋怨看榜的兵丁:“你们这些东西真可恶,怎么把法官给捆来了!”赶紧过去,亲自松绑。屋里就一个座儿,解大人道:“法官请坐吧。”应该是帅不离位呀,孙德龙也不懂,一屁股就坐下啦;坐下不算,他这话可气。“哎!你坐哪儿呀?”解大人说:“那我就站着吧。”“我说大人啊!这老道咱上哪儿找他去?”“他住在江米巷金台馆驿。走吧,你先跟我见驾去吧。”“见哪个驾呀?”“见皇上去呀。”“那太好了,我们哥儿俩有日子没见了。”跟皇上哥儿俩!“法官,咱们进宫您是骑马呀,是坐轿啊?”“全不用。”“全不用?用什么法术?”“骑驴。”“骑驴哪给您找去呀?!”“没驴我不去了。”解大人没法子,打广安门雇了匹赶脚的小驴儿。到了宫里头,让孙德龙到东朝房候旨。
解大人去见驾,皇上十分喜悦,吩咐即刻召见。解大人一想:不能让他见驾——还没到礼部演礼,嘴里头不定说出什么来,回头见了皇上一作揖,“咱哥们老没见了”!我这纱帽也就丢了。赶紧就说:“万岁!法官是外省人,初到京城,未在礼部演礼,恐有失仪。依臣之见,找来老道先斗法,斗法之后再见驾也不为晚。要是赢了老道,见驾时倘有失仪,我皇万岁也能谅情一二。”
当时就派人从金台馆驿把老道找来,告诉他,我国有人跟你斗法。老道出主意,就在太和殿前高搭两座法台,都要三丈多高,上头预备八仙桌子一张,太师椅一把,香炉、五供、蜡扦、黄毛边纸、朱砂笔、香菜、五谷杂粮,还有一碗无根水。“你家法官需用何物你去问他。”解大人一琢磨,干脆也给他预备这么一份得了。人多好做活,当时法台搭好,东西也预备齐了。老道一抖袍袖,有一股黑旋风就把他托上了法台了,文武百官目瞪口呆。
皇上传旨:“叫解大人去请咱们的法官眼老道斗法,也让咱们法官驾风或者驾云上法台。”解大人赶紧跑到东朝房去找法官,进屋里一瞧哇,法官躺在地上睡着了。解大人赶紧过去叫:“法官,起来!”“别闹!”“谁跟你闹了!把他搀起来。”孙掌柜揉了揉眼睛往四外一看,这是皇宫里头,金碧交辉,富丽堂皇。“哎,老大人!这是哪个场儿?”“皇宫内院。”“我上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啊!你忘了,你不是找老道斗法来了吗?现在老道在法台上等着你呢。皇上宝座升到殿外,要看你二人如何斗法。”孙掌柜一听可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刚才他撕皇榜的时候酒喝得十成醉,在地上睡了半天觉,酒气儿冰下去了,把刚才撕皇榜那碴儿全忘了。现在听解大入这么一说,自己一想:我喝酒喝得太多了,酒后闹事撕了皇榜,我是买卖人,卖猪肉的,哪儿会跟老道斗法呀!再说这老道是打外国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这不是捅漏子吗?想到这儿,左右开弓,啪啪啪啪!自己打了四个嘴巴:“我胡涂,我胡涂!”往后一退步,咕咚脆下了:“老大人哪,我喝多了,我撕皇榜是耍酒疯儿,我是个买卖人,就懂得卖猪肉。斗法这个事儿干脆你找别人吧!这个事儿,我是办不了啊。你若不出气的话,你给我俩嘴巴,你拿我当个风筝——把我放了吧!”啊!?解大人一听连生气带害怕,浑身直抖,帽翅乱动。赶紧就说:“哦,你喝多了,你这个酒喝得太凶了,你摸摸你还有脑袋没有?我给你俩嘴巴把你放了就完啦?你跟我这么说行了,我在万岁驾前要是这么说呀,是欺君误国,欺君事小,误国事大。现在老道已经来了,皇上拿什么话来回答他呀?这么大国家因为你失了信用,咱俩人全活不了,你是酗酒闹事撕皇榜,戏耍看榜钦差大臣;我是办事不力,错引平民入宫,欺君误国。咱两个人的死,罪有应得,祸由自取,皇上跟着丢人!偌大中国失去天威,琉球为上邦,我大明为属国,咱们就全成了亡国奴了。”孙德龙跪着这么一听,他可急了:“哎,这不是没有的事吗?我这点酒怎么惹这么大祸呀?哼,不单皇上丢人,连全国老百姓也跟着丢人。咳!”啪!他一拍胸口,刚才喝的那点酒又都撞上来了,跪着好好的,蹭楞他蹦起来了:“老大人呀!不要紧!照你这一说咱俩不就没了命了吗?没命就好办了,我不找老道斗法不是也活不了吗?这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脑袋掉了不是才碗大的疤瘌吗?别看跟老道斗法不行,打?他还不准是个儿那!咱找他去。走!”解大人一听:“你到底会不会呀?”“咳,你就走吧!”
解大人也没办法了,只好把他领到法台下边,用手一指东边的这座法台:“你看!老道已经在上边打上坐了。”孙德龙一瞧:“老大人,他上那边,我就上这边儿了,我们俩要是上一边儿,那为争地盘儿不就打起来了吗!”“快上吧!”“这法台有多高?”“三丈三!”“三丈三哪?九丈九也不要紧哪。来人!”“干吗呀?”“搬梯子。”“搬梯子可不行,皇上已经传过旨了,或是驾风或是驾云,因为老道是驾风上去的。”其实呀,老道也不是驾风。那末你刚才说,不是一抖袍袖有股黑旋风裹着老道上去的吗?那是个戏法儿。在他袖口儿里边有个铁筒儿,铁筒里头装的是狼粪、大青、炭饼,把它点着了。用的时候,他一抖袍袖,就把那盖儿打开了,你想他穿的是道袍,大领儿,这些个黑烟,顺脖子、大襟、底襟全冒出来了,狼粪点着了不散,大青这昧药点着了净冒黑烟,好象黑旋风裹着他一样。手上脚上都有小铁钩,他是顺着法台的杉篱爬上去的!孙德一听说驾风驾云,就问解大人:“老大人,我驾什么风呀?”“趁脚风呗。”“我会抽羊角疯。”“那没用。”“咳,干脆,没梯子我不去了。”“哎,别价呀。”孙德龙着急了,就要往法口前边转。“别往前边去,皇上在前边哪。”“我喽喽。”解大人一听,有喽皇上的吗?“坐那儿那个人儿是谁呀?”“那就是皇上啊。”“旁边那站着八个大个儿,是干什么的?”“那是保驾的,金瓜武士。”“他手里举着的那是什么?”“那就是金瓜。”“你把那头一个顶高个儿的叫过来我有事儿。”解大人过去一瞧,这位是太和殿头等侍卫白文元白老爷。“白老爷,过来我给您引见个朋友。这位是来斗法的孙法官。这位就是太和殿头等侍卫白文元白老爷。”“哦,白大人,你好啊,请你帮忙吧。”“什么事哪?”“我上法台。”“与我有什么关系呀?”“没你我上不去呀。”“怎么哪?”“你想啊,这法台三丈三,你多高身量?”“我呀?皇上选最高个儿的,身高九尺。”“你手里举的这个金瓜多长?”“一丈四的瓜把儿,一尺的瓜头,一共一丈五。”“啊,对呀!一丈五,身高九尺,就是两丈四,胳膊伸长了二尺,两丈六、三丈三一一差不离儿了。”白大人一听:他这儿算什么哪?“啊,你把这瓜放平喽,你两手攥住瓜把儿,我坐在瓜头上你不能把我扔上去呀?”“这……没听说过。”“你要是不扔我可走啦!”解太人赶紧跑过来说:“白大人,您受累试试看吧。”白文元气得直抖手,这叫什么事啊!也没办法,只好试试看,就把金瓜放平喽,两手抓住瓜把儿,说:“来吧!”孙德龙坐到瓜头上,自老爷说:“您提着点气可别往下坠。',白老爷运足了气力:“我可要扔了啊!啊嘿!”这一下子真不含糊,法台三丈三,扔上有四丈四去。过了法台还一丈多哪。就由这一丈多高掉下来呀,法台都是二寸多厚的板子,摔不死也得摔个半死。该着这个老道倒霉,孙德龙没摔着,不但没摔着,并且还站到法台上去了。那位说,你说的这个不合理,他扔上去往下落,怎么也得腰朝下,那就是躺到那儿了,怎么能站着呢?这里头有个原因:他胳肢窝夹着一个搭猪的钩竿子,有五尺多长,您想啊,他过了法台一丈一,从这一丈一往台上落的时候,落下五尺多,钩竿子把儿就戳到台板上了。胳肢窝夹着钩竿子往下一出溜,脚就踩着台板了。手一拧钩竿子,嗨!他站住了。
这个老道啊,就在对面法台上闭目合睛打坐养神,孙德龙怎么来的,怎么坐着金瓜往上扔,他全不知道。他睁眼的工夫,正是孙德龙由一丈一往下落的时候,老道一看就害怕了:哎呀,了不得,中国真有高人。贫道驾着风上法台,怎么中国的法官会从;天而降哪!——扔上来的他没瞧见。老道再一看孙掌柜,他更害怕了:这位法官是足踏祥云,金光护体呀!——足踏祥云那是孙掌柜没站稳,把香炉拨拉到台上了,香灰这么一扑,跟云彩-样;那金光护体呢?是孙掌柜那件油棉袍,太阳一照猪油放光!您说这老道不是倒霉催的吗?!打仗是怯敌必败,他吓得直哆嗦,肝儿都颤了。老道一想:这可得多加留神。越留神越坏。老道单手打稽首,口念:“元量佛!”别看他身量矮,声如铜钟。老道一念佛,孙掌柜一想我也得说一句呀:“啊,好家伙!”人家念无量佛,他念好家伙。老道又念了一句:“无量……寿佛。”孙掌柜一听:噢,加字儿啦?我也加字儿:“一大堆破烂家伙!”
老道一听:他这家伙还真不少,我没那么多家伙,干脆跟他打哑谜得了。冲孙掌柜伸出一个手指头去,这就是哑谜。老道是说:你别瞧不起我,我有“一佛顶礼”。孙掌柜不懂啊,他撕皇榜的时候不是说会打哑谜吗?可是他打那哑谜跟老道这个不一样啊,他是肉市上卖猪肉的,这个猪多大分量、多少钱、多少整、多少零,两人拉拉手儿,是这个哑谜。他一看老道伸了一个大拇指:这是干什么?伸一个手指头……噢,要跟我喝酒划拳哪!没关系,来,你看这个!——他伸出俩手指头来,他是什么意思哪:你“独占一”呀?我“哥俩好”——嘿,他划上拳啦!这下老道可害了怕啦!哎呀!我伸一个手指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是“二圣护身”哪——让他给蒙上来啦。老道又伸了三个手指头,那意思是说“三皇治世”。孙德龙这儿又琢磨了:什么?“三大元”?好,“五魁首”!——他伸了五个手指头!老道一看:嗯,对!“三皇治世”正对“五帝为君”哪。——全弄到两下去啦!老道一拍心口,他是说:“佛在心头坐”。孙掌柜一瞧:好小子,你拍胸口,怎么,你还不服气?(手拍脑袋一下)啊嘿!他那意思是说,我也不怕你!老道一看:哟,我“佛在心头坐”,他“头上有青天”哪。——满弄拧了!
老道一看,打哑谜我赢不了他了。拿过一张黄毛边纸来,嗤楞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孙德龙一看:“干什么?要抹脖子呀?”老道把纸裁了三条儿,用朱砂笔刷刷刷画了三道符,火绒火石打着了,把蜡点着,用宝剑尖儿扎起一道符来,在蜡火上一点,口中念念有词,一晃这宝剑,这团火越晃越大,他要火烧孙德龙。孙掌柜还开玩笑哪:“嚯嚯嚯嚯嚯,老道,那么大个子别玩火呀,玩火睡觉尿炕,妈妈打屁股。”老道这个气呀!这团火光有茶杯粗细,晃来晃去就有冰盘大小了。按理说,这道符就那么一个纸条儿,沾火就完了。为什么这火越晃越大呢?其实并不是念咒念的,画符的朱砂里头有药材,所以火越烧越大。到了冰盘大小,这团火就甩过去了,直奔孙掌柜面门,孙掌柜往旁边一斜身儿,一歪脑袋:“好小子,烧人哪!”明朝人是拢发包巾,这团火擦着孙掌柜的耳根台子,过去的,磁啦一下,烧去了半边发罄。孙掌柜用手一胡噜,把手也烫了。桌上有一碗无根水,这碗凉水救了命啦!往脑袋上一浇,哗!火灭了。老道一看头道灵符没成功,再来一张,把第二道符点着了,孙掌柜一瞧:“好小子,得理不让人啊,烧完这半拉再烧那半拉,一根头发没有了。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咱俩一块儿化缘去。我不想出家呀!别等他再烧我了,我先给小子一钩竿子吧。”顺手抄起钩竿子来,冲着老道面门瞄准。老道装模作样,闭着眼睛,摇晃脑袋,嘴里嘟嘟囔囔装着在那儿念咒,他这一闭眼睛,孙掌柜得搂了。怎么?他好瞄准呀!拿着钩竿子来回悠达,悠达欢了,这叫杆儿朝前,钩在后,觑着目,往对过儿瞅,对准了前拳撒后手儿。他说:“着家伙!”他要是不喊这句呀,正打到老道的面门上;他这一喊,老道睁眼一看,直戳戳一俨栅门而来。“无量佛!”往旁边一斜身儿,还算好,没打着。您可听明白喽,杆是没打着,后头这俩钩儿可不饶人哪,喽哧一下正钩到腮帮子上。往下一拨钩竿子,带下两条子肉来,疼得老道捂着腮帮子直念:“无量受不了的佛!”孙掌柜还跟着起哄哪:“不留神,挨家伙!”老道这个气呀!再一看钩竿子,他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心里更害怕了:“哎呀,我太不识时务了。刚才那位法官来的时候,足踏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这一定是十八罗汉大罗金仙。现在一看果然是大罗金仙,若不然怎么能把西天如来佛的八宝如意紫金钩拿来?!”其实,那是搭猪用的!
孙掌柜可乐了:“小子,你把我头发烧了还能长啊,你这腮帮子破了,锅碗的不会补啊!”他这心里一痛快,可高兴了。老道更害怕了:头道符我烧了他半边发害,二道符未曾发用,他就打了我一八宝如意紫金钩。再一瞧孙掌柜那儿提溜着一个钱口袋,老道更嘀咕了:他还带着百宝囊哪!再一看,孙掌柜腰里头拴着把酒壶。好家伙!还挂着翻天印哪!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瞧什么都有用啦!越琢磨越害怕,干脆,三十六着——走!“无量佛,贫道我要回国交旨。”“哎!你要是走我可祭法宝!”“别价!我先去见你家万岁爷。”说完这话一抖袍袖,冒出黑烟,变了个戏法就下台了。老道走到太和殿前往那儿一跪,磕头如同捣蒜:“天邦大国万岁开恩,小国使臣前来请罪。”皇上那儿看得明白呀!可是他俩打的哑谜念的什么“无量佛”、“好家伙,,这全不懂;又瞧老道拿火烧人,孙掌柜拿水把火烧灭了,皇上高兴了:“好!水能克火。”再看老道又点起火来了,心想:讨厌的东西,你已经赢了何必赶尽杀绝。皇上净顾瞧这火了,没看见钩竿子怎么过去的,一瞧老道腮帮子流血了,皇上拍着巴掌直乐:“我国法官得胜了。好法宝!好法宝!”现在一看老道下来了,皇上明白,这是他输了,说:“了义真人,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讲?”“啊呀!天邦大国万岁开恩。敝国认输,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嗯!我得问问你,你们俩见面说‘无量佛,这是怎么句话?”“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见面礼儿。”“那么他说那‘好家伙,哪?”“那我实在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好家伙。”“那么你说那‘无量寿佛,哪?”“这是问候。”“那我国法官说那句‘一大堆破烂家伙,哪?”“那想必是贵国法官家伙太多了。”一指腮帮子,“我这不挨了一家伙吗!”“后来你不说话,伸出一个手指头是怎么回事?”“是打哑谜,我说的是‘一佛顶礼’。”“我国法官伸俩呢?”“他说他有‘二圣护身'。”“你伸仨呢?”“‘三皇治世'。你家法官又伸五个,他说有‘五帝为君’;我一拍胸口说‘佛在心头坐',他一拍脑袋,说他‘头上有青天’。”——嘿!全蒙对了!皇上说:“那么你那火是怎么回事情?”“万岁开恩,我是想把贵国法官烧下法台。”“哼!出家人不讲慈悲,脸上是被什么伤的?”“八宝如意紫金钩。”他就不知道是搭猪用的,跪在一旁听候发落。
皇上往法台上一看,忙跟解大人说:“咱们的法官怎么还不下来呀?”他得下得来呀!孙掌柜在台上转磨:“哎!这是怎么回事?倒是输了赢了?”他还不知道哪!皇上一瞧,说:“想必我家法宫、被魔火烧伤,赶快派人把法官接下法台。”皇上这句话积大德了。刚才扔上去的,这要是往下一跳非摔死不可。皇上一说把他接下来,有人立好了云梯,孙掌柜顺梯子就下来了。解大人过来说:“走,跟我见皇上去,要多磕头少说话。”怎么哪?怕他见皇上再来个“咱哥俩老没见了”!孙德龙到了太和殿前,冲皇上作了个大揖:“嗬!”皇上一瞧: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咱给老皇上磕头了。”他这一赢,皇上高兴:“法官抬起头来。”别人都得说“有罪不敢抬头,',等皇上说“恕你无罪”,这才抬头,孙掌柜满不懂,一抬头直眉瞪眼瞧着皇上:“干什么?”上人见喜,皇上乐了:“法官你斗法是输了是赢了?”孙掌柜就怕问这句,输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低下头去,装没听见。他这一低头,皇上又问:“你输了你赢了?”他往旁边一看,正瞧见老道。正赶上这时候皇上问第三句:“法官!你跟老道斗法是输了是赢了?”“我说皇上,你老人家问我输了赢了,这个话我不好说呀!怎么呢?我要是说我赢了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可我要是说我输了吧,我干什么来了?没有金钢钻就不敢揽瓷器!”解大人一听:你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呀!“你老人家问我输了赢了,你别问我。”一指老道,“你问他!他说我输了就算我输了,他说我赢了就算我赢了。老道!你要是说我输了,咱俩上台再来来!”老道一捂腮帮子:“别来了!他赢了。”“皇上听见了吧?我赢了!我赢了!”皇上问:“法官,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孙,叫孙德龙。肉市德龙馆那个小买卖是我开的,咱是准斤十六两绝不少给分量。”——谁问你这个了!“你们俩一见面,他说‘无量佛;是怎么回事?”“这‘无量佛’是怎么句话?皇上,这个老道我认得。”老道一听吓了一跳:他认得我,我怎么不认得他呀?你哪儿认得去,他是卖猪肉的!“这个老道是化缘的。”“化缘干吗说‘无量佛’呢?”“我开肉馆子,他们化缘,和尚念‘弥陀佛',老道念‘无量佛’,就是跟我要钱哪。”“那么你说那‘好家伙’哪?”“我说‘好家伙’,是心里想,怎么刚走俩化缘的又来一个?”老道听着这通窝心哪!“那么你们俩人打哑谜,他伸一个手指头是怎么回事情?”孙掌柜一听:这回可糟了,怎么说呀?老道伸一个手指头,是“独占一”,我“哥俩好”,“三大元”、“五魁首”?合着我们俩没斗法,在哪儿划拳哪!这不象话呀。得啦,干脆我瞎编个词儿吧。这一编词把老道给送下来了。“皇上,他没跟我打哑谜!”皇上说:“怎么?,他伸一个你伸俩,他伸仨你伸五个,他一拍心口你一拍脑袋,这不是打哑谜吗?”“不!我俩是讲买卖呢!”“讲什么买卖呀?”“老道知道我是肉市上卖猪肉的,他庙里头办喜事,他想买我一口猪。”老道心说:我多咱想买他一口猪哇!皇上问:“那么你伸俩手指头呢?”“我说别说你买一口猪,买俩我也有啊!他说要个三十来斤的,我想,我那儿顶少也有五十多斤呀;他说可得带下水——心肝肺,我一拍脑袋,那意思是说:甭说心肝肺,(手拍脑袋一下)连猪头都是你的呀!”
得,满拧!
标签:刘宝瑞,斗法